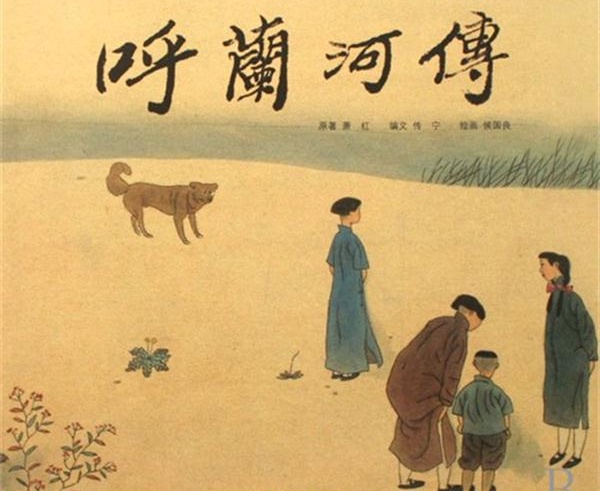
《呼蘭河傳》雖然定義的是小說,但寫法與別的小說卻很不相同,一般的小說都會有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貫穿全書,但《呼蘭河傳》沒有。
它用詩一樣的語言,散文一樣的結構,從一個孩子的視角去描寫她家鄉的風土人情和人物的生活場景。讀著就像是由一篇篇回憶兒時的精彩散文組成。正如矛盾先生評論這本書所說的:“《呼蘭河傳》不像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小說,而在于它這“不像”之外,還有別的東西,一些比“像”小說更為“誘人的東西,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
說到這部小說,就不能不說說作者蕭紅的身世。蕭紅1911年出生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呼蘭區一個地主家庭,是“民國四大才女”之一,被譽為“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洛神”。魯迅先生評價她“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可惜因病于1942年逝于香港,年僅31歲。但她短暫的一生卻因她筆下的文字而長存于后世之人心中。
著名文藝理論家胡風評價說,“蕭紅寫的都是生活,她的人物是從生活里提煉出來的、活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我們產生共鳴,好像我們都很熟悉似的。”
讀蕭紅的文字,確實有這種感覺。與同樣是“民國四大才女”之一的張愛玲的文字是完全不同的寫作風格。張愛玲的文字讀著覺得清冷、華麗,有種一般人無法企及的高度。而蕭紅的文字讀著覺得真實、貼近生活,更易引起讀者的共鳴。
而我尤其喜歡她筆下對景物的描寫,在《呼蘭河傳》里,就有大量描寫景物的筆墨,那些本沒有生命力的景物,卻在蕭紅的筆下,全都活靈活現起來,作者似乎賦予了它們獨特的生命,一起來感受一下。
寒冷冬天的描寫
大地一到了這嚴寒的季節,一切都變了樣,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風之后,呈著一種混沌沌的氣象,而且整天飛著清雪。人們走起路來是快的,嘴里邊的呼吸,一遇到了嚴寒好像冒著煙似的。七匹馬拉著一輛大車,在曠野上成串的一輛挨著一輛地跑,打著燈籠,甩著大鞭子,天空掛著三星。跑了兩里路之后,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這一批人馬在冰天雪地里邊竟熱氣騰騰的了。一直到太陽出來,進了棧房,那些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馬毛立刻就上了霜。
嘴里冒煙、天空掛著三星、馬毛上霜。這段描寫,把東北特有的那種寒冷淋漓盡致的表現了出來,讓身在南方的我幾乎真切的感受到了那種刺骨的寒冷。就是這種寒冷把大地凍裂了,把水缸凍裂了,把人的手也凍裂了。
火燒云的描寫
“天空的云,從西邊一直燒到東邊,紅堂堂的,好像是天著了火。
這地方的火燒云變化極多,一會紅堂堂的了,一會金洞洞的了,一會半紫半黃的,一會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大黃梨、紫茄子,這些顏色天空上邊都有。還有些說也說不出來的,見也未曾見過的,諸多種的顏色。
五秒鐘之內,天空里有一匹馬,馬頭向南,馬尾向西,那馬是跪著的,像是在等著有人騎到它的背上,它才站起來。再過一秒鐘,沒有什么變化。
再過兩三秒鐘,那匹馬加大了,馬腿也伸開了,馬脖子也長了,但是一條馬尾巴卻不見了。
讀這段時,直覺得把那虛無的火燒云寫活了,形狀各異的小豬、小狗、小馬、獅子輪番上演。小時候生活在農村,天空上這樣的場景我是見過的,那火紅的云彩就像會魔術似的千變萬化,不過是片刻,那云已經不知道變了幾個樣子。”
后花園的描寫
“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鳥飛了,就像鳥上天了似的。蟲子叫了,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無限的本領,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樣,就怎么樣。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黃瓜愿意開一個謊花,就開一個謊花,愿意結一個黃瓜,就結一個黃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個黃瓜也不結,一朵花也不開,也沒有人問它。
玉米愿意長多高就長多高,他若愿意長上天去,也沒有人管。蝴蝶隨意的飛,一會從墻頭上飛來一對黃蝴蝶,一會又從墻頭上飛走了一個白蝴蝶。它們是從誰家來的,又飛到誰家去?太陽也不知道這個。只是天空藍悠悠的,又高又遠。”
看似很隨意的文字,卻把我帶進了那個充滿生命力的花園里,花園里的一切似乎都是有思想的。花是有思想的,鳥是有思想的,倭瓜是有思想的,黃瓜是有思想的,玉米是有思想的,蝴蝶也是有思想的。它們都按各自喜歡的方式活著。
磨房窗子的描寫
“下了雨,那蒿草的梢上都冒著煙,雨本來下得不很大,若一看那蒿草,好像那雨下得特別大似的。
下了毛毛雨,那蒿草上就迷漫得朦朦朧朧的,像是已經來了大霧,或者像是要變天了,好像是下了霜的早晨,混混沌沌的,在蒸騰著白煙。
刮風和下雨,這院子是很荒涼的了。就是晴天,多大的太陽照在上空,這院子也一樣是荒涼的。沒有什么顯眼耀目的裝飾,沒有人工設置過的一點痕跡,什么都是任其自然,愿意東,就東,愿意西,就西。若是純然能夠做到這樣,倒也保存了原始的風景。但不對的,這算什么風景呢?東邊堆著一堆朽木頭,西邊扔著一片亂柴火。左門旁排著一大片舊磚頭,右門邊曬著一片沙泥土。
這是一個荒涼無比的院子,蒿草滿院、凌亂不堪,可里面依然住著各色各樣的人,養豬的、開粉房的、開磨房的、趕車的,他們用渺小卑微的生命在這個荒涼的院子里演繹了一出出的悲歡離合。
那磨房的窗子臨著我家的后園。我家的后園四周的墻根上,都種著倭瓜、西葫蘆或是黃瓜等類會爬蔓子的植物;倭瓜爬上墻頭了,在墻上開起花來了,有的竟越過了高墻爬到街上去,向著大街開了一朵火黃的黃花。因此那廚房的窗子上,也就爬滿了那頂會爬蔓子的黃瓜了。黃瓜的小細蔓,細得像銀絲似的,太陽一來了的時候,那小細蔓閃眼湛亮,那蔓梢干凈得好像用黃蠟抽成的絲子,一棵黃瓜秧上伸出來無數的這樣的絲子。絲蔓的尖頂每棵都是掉轉頭來向回卷曲著,好像是說它們雖然勇敢,大樹,野草,墻頭,窗欞,到處的亂爬,但到底它們也懷著恐懼的心理。”
磨房本是很寂寞的,沒有生命的。可因了倭瓜、西葫蘆、黃瓜這些爬蔓子延伸過來的小細蔓,磨房的這扇窗子立即充滿了生命的氣息,讓人感受到了旺盛的生命力,那寂寞的磨房立即鮮活了起來。
這些原本很平常的景物,在蕭紅的筆下,都變得鮮活立體起來,讀來令人意猶未盡。
蕭紅用一支筆記錄下了中國東北那座叫“呼蘭河”的小城,小城里有她童年時的美好回憶,回憶里有她家寬大而嘈雜的院子,院子里有個繁茂而荒涼的后花園,后花園里有她最溫馨的記憶,記憶里還有這些鮮活的平常景物。
這些,一并都被她記在那本薄薄的《呼蘭河傳》上了,也深深的銘記在我們這些喜愛她的讀者心中了。
上一篇:李緣
下一篇:文旅部提醒:近期切勿前往美國旅游





